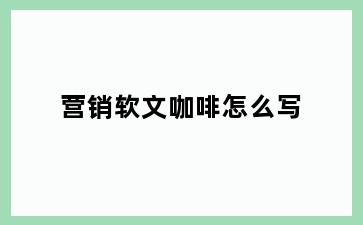营销软文咖啡-咖啡的软文营销
Time:2025-07-26 11:41:18
关于营销软文咖啡的问题,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给你解答:
营销软文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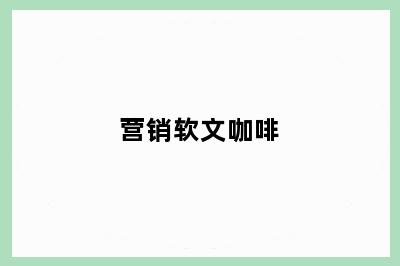
1928年,著名的《语丝》杂志刊登了郁达夫所作《革命广告》一文:
郁达夫在文中写道,近日看《申报》上出现咖啡馆的广告,号称在这革命的咖啡馆里,能遇到许多革命文艺界的名流,革命的郁达夫和革命的鲁迅等等。他便驳斥说,他作为一个“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郁达夫,没钱去奢华的咖啡馆,更不知道这上海还有个革命的郁达夫;同样,他只听说过一个不革命的老人鲁迅,既然“老”就不够革命,甚至是反革命。郁达夫尖刻地讽刺了这种借“革命”名义经商赚钱的广告,鄙夷之情溢于纸上: “现在革命最流行,在无论什么名词上面,加上一个‘革命’,就可以出名,如革命文艺、革命早饭、革命午餐、革命大小便之类。”
另一位民国大V鲁迅在这篇文章后面补了附记,也是他的惯常风格——一本正经地嘲讽,毫不留情地揭露,将咖啡馆的小心思给掀了个底儿掉: “上海滩上,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多。大如弄几本杂志,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喫冰淇淋。虽然我至今还猜不透那些惠顾的人们,究竟是在意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至于咖啡店,先前只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还有‘教益’,还演‘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
那么两位文豪批判的,到底是怎样一家咖啡馆呢?笔者生了好奇,便翻阅了《申报》1928年8月的内容,找到了这家“上海珈琲”的若干广告。
其一是图片广告,地址是北四川路518号,与郁达夫文中所提一致,还特意作了“女子招待、格外有趣”的噱头;
其二是文字广告,署名慎之,先是抱怨了一番上海的消闲去处浮俗吵闹、不够档次,然后转而推荐——“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领会到不少教益呢。”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这可以说是篇相当合格的软文了。这两份广告篇幅又小又不显眼,其实也没有过分吹嘘加戏,何以受到两位文豪的合力调侃呢?
其实文章背后,隐藏着鲁迅、郁达夫与创造社的一段复杂纠葛。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一个著名的新文学团体,1921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在东京创立。其成员原本大都倾向于革命,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受“左”倾路线和思潮的影响,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日趋激进,一度揭橥“革命文学”的旗帜,与主张相近的太阳社联合,在文艺界展开大批判,鲁迅、茅盾、叶圣陶及脱离创造社不久的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曾成为他们的重点批判对象。鲁迅、郁达夫在文章中自称“不革命”、“反革命”、“小资产阶级”、“有闲阶级”“落伍者”等等,其实都是此前创造社、太阳社给他们贴的标签。
上文所提这家“上海珈琲”正是创造社所开办。而且,文中所提到的作家,除了鲁迅和郁达夫外,冯乃超、龚冰庐、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都是创造社或太阳社的成员,就连文章的作者“慎之”(当即黄慎之),也是创造社刊物的撰稿人。作为论敌,鲁迅、郁达夫怎么肯与他们“同流合污”呢?
鲁迅和郁达夫虽与创造社针锋相对,但在文章中还是给对方留了些余地,未明白点出其名,外人难免不明就里。鲁迅在给友人章廷谦的信里就写的很清楚:
“创造社开了咖啡店,宣传在‘那里面,可以遇见鲁迅、郁达夫’,不远在《语丝》上,我们就要订正。田汉也开咖啡店,广告云,有‘了解文学趣味之女侍’,一伙女侍,在店里和饮客大谈文学、思想,好不肉麻煞人也。”
这样一看,似乎鲁迅是不喝咖啡的。然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糟老头子文学大师坏得很,不可信了他的邪。事实上他不但喝过咖啡,而且喝得甚早。清末留日时他有没有喝咖啡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民初他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时,是不止一次地喝过的,有日记为证:
1913年5月28日:“下午同许季上往观音寺街晋和祥饮加非。”
1914年1月10日:“午与齐寿山、徐吉轩、戴芦苓往益昌食面包、加非。”
鲁迅在日记中通常都写作“加非”或“加菲”。从日记看,鲁迅在北京的时候,喝咖啡虽然不很频繁,但也并不排斥,偶尔一饮。又如1920年5月26日,曾与二弟周作人“同至店饮冰加非”;1923年8月1日,“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馆小坐”。因为咖啡味苦,有人将其与相思、悲苦、离愁等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意象相联系。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中,更有一些人喝着咖啡自称“颓废派”,鲁迅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对他们给予了“可笑”的评价,作为一位硬核文人,他自然看不上这种矫揉造作的小清新。
1927年鲁迅离开厦门来到上海的时候,郁达夫曾约他和许广平、许钦文一起吃饭,饭后喝的就是咖啡。当时鲁迅还用“告诫亲属似的热情的口气”劝说“胃不行”的女友“密斯许”(许广平),“咖啡还是不吃的好”,郁达夫则从这一细节中“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鲁迅的朋友圈
喝咖啡本身又不是什么丑事,在当时的上海,还是风雅时尚之举呢。作为舶来饮品,咖啡早在清朝末叶就开始出现在上海等地的外国租界中。1887年印行的《申江百咏》中有这么一首竹枝词:
“几家番馆掩朱扉,煨鸽牛排不厌肥;一客一盆凭大嚼,饱来随意饮高馡。”
诗中的“番馆”指的是西餐馆,而“高馡”就是咖啡。西餐馆的客人们一人一份烤乳鸽或者牛排大快朵颐,餐后享用一杯咖啡以助消食,这和今日西餐厅的景象并无二致,可见那时喝咖啡这种“摩登”事物已经开始在上海流行了。
咖啡馆的存在意义,从来不仅仅是为了餐饮,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就把它当作“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代表性场所。自诞生之日起,咖啡馆就很自然地成为一个疏离于体制外的公共空间,为社会各界精英提供了交流和讨论的途径。例如巴黎左岸的普罗科普(Le Proceope)咖啡馆,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发表过他们的思想;维也纳大学边上的中央咖啡馆(caf Central)里,列宁、托洛茨基等革命家、薛定谔、哥德尔等科学家、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文化名人都曾在此流连。随着沪上咖啡文化的兴起,备受欧美革命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也将眼光投向了这片尚不引人注目的乐土。时事所趋,鲁迅后来成了北四川路上一家公啡咖啡馆的常客,公啡咖啡馆也因为鲁迅的时常光顾而声名大振。1930年2月16日的“左联”筹备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鲁迅也出席了会议,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午后同柔石、(冯)雪峰出街饮加菲。”后来,鲁迅和左联同志们经常在这里聚谈、议事。
此时的咖啡馆,已不再是鲁迅笔下嘲讽批判的对象了,反而成为他进行创作和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真正与革命产生了关联。据说傲娇的鲁迅先生就是因为之前声明过“不爱咖啡爱绿茶”,所以也不好意思自己“打脸”,刚开始还带着茶壶去,去得多了也不愿多费周章,也时常会来一杯。
由此看来,与其要说郁达夫和鲁迅对有奢华、颓靡之嫌的咖啡馆有意见,不如说是他们对当时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人的姿态深恶痛绝。他们以为,这帮所谓的“革命文艺界人士”坐在咖啡馆里,喝着谈着,指点着“龌龊的农工大众”,这样所谓的新文化是荒谬的。用咖啡消费和休闲的群体高谈阔论着,真正需要革命来改善境遇的无产阶级,却无缘享受所谓“革命”的咖啡。这种咖啡店实际是如何光景呢?1929年2月5日《申报》第十五版有一则报道可为管窥,题为《大学教员与女招待冲突》,抄录如下:
“北四川路口上海咖啡店内,雇有妙龄女郎周云仙、陈素芬、汪秀英等三人为女招待,因此一般青年子弟趋之若鹜,营业甚盛,但胡调打架之事在所难免。前日有某大学教员王英前往该咖啡店果腹,不知如何,与此三女招待大起冲突,而致互殴,咖啡店中器具毁坏甚多……”
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个结识名家、获取教益的革命乐园呢。
鲁迅永远是警惕着的,他不但警惕着政治对知识分子的威逼利诱,也警惕着商业编织的消费主义陷阱。广告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销售,商业利润是其唯一追求,那么无论广告词用多么时髦的字眼和循循善诱的腔调,“革命”、“救国”、“新生活”之类,以及如何利用当时的新潮和时事,商业其实都是漠不关心的,不过是以此为幌子招徕顾客。例如某卖中药的厂家,广告词曰“阮玲玉之死因为人言可畏,眼下暑热可畏,欢迎购买防暑药品。”如此生硬的“蹭热点”,哪个时代都要嫌弃的。《语丝》本是不接广告的,但转刊到上海后迫于无奈被加了些广告,鲁迅也是颇为不满。后来在《萌芽》发表文章谈到广告问题时,他写道:
“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子的小报,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读者,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现在不过用男作家,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或捧或骂,算是在文坛上做工夫。”
显然,鲁迅反对的既不是咖啡,也不是革命,而是这种“打旗子”、“作幌子”的行为。资产阶级文人们把“革命”当作为自己沽名钓誉的工具,把自己对西式现代生活的追求和物质欲望包裹成一种进步的姿态,歪曲了革命本身的意义,也无法将革命的价值传递给民众,自然被真正的革命者所不齿。
九十多年过去了,革命咖啡馆风波所折射出的人情世态,如今亦不鲜见。明明就是些一心赚钱的营生,为了招徕热度和流量,树一些诸如“民族品牌”、“环保事业”、“自我提升”的冠冕牌坊。拉大旗作虎皮还则罢了,有些还要去害人,这就殊为可恨,愿诸君明鉴。
咖啡的软文营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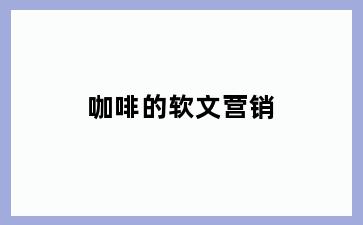
写作 最快乐的事 莫过于让作品成为阅读者心中的光芒 透过行走 人们与我分享他们的 勇敢 梦想 希望 这让我感动 写下他们的故事 只要你敢,总会有光芒指引你. 活出敢性(live out your boldness) 雀巢咖啡! 纸上写的那一段有些好像没有实际意义,显露出来的只有 【就算你骑着摩托飞驰 总有 光芒引你去 清澈的地方——韩寒】
营销软文咖啡怎么写